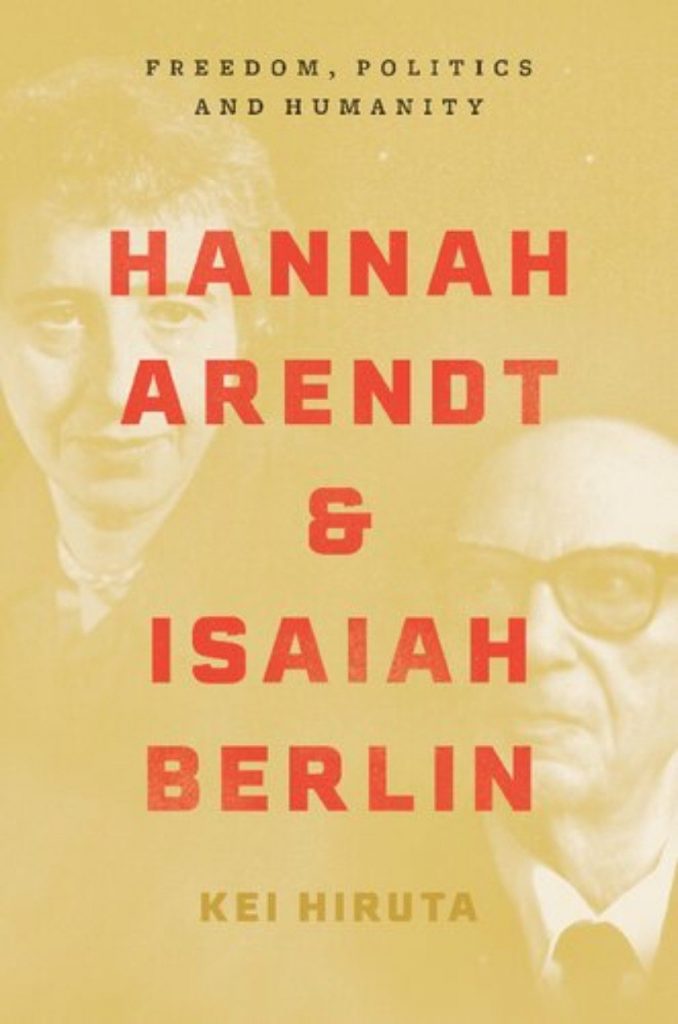我們一般都喜歡看Berlin的論自由等作品,而事實上他的書被翻譯成中文的也真不少。同樣,我們也會喜歡看Hannah Arendt的書,尤其那本討論平庸的惡的” Eichmann in Jerusalem”。但當我們看到Berlin在“Conventions with Berlin”、“Personal Impressions”對Arendt的極厭惡的態度時我們可能會感到錯愕
” 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第一次完整地講述了 20 世紀最重要的兩位思想家之間的衝突——以及他們深刻的分歧如何繼續為政治理論和哲學提供重要的教訓
20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兩位思想家Hannah Arendt,1906-1975和Isaiah Berlin,1909-1997在政治、歷史和哲學的核心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儘管他們作為猶太移民知識分子的生活和經歷重疊,但Berlin非常不喜歡Arendt,稱她代表了“我最討厭的一切”,而Arendt則以冷漠和懷疑的態度對待Berlin的敵意。”
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一書以生動的風格寫成,充滿戲劇性、悲劇性和激情,首次講述了這些大人物之間令人擔憂的關係的完整故事,並展示了他們截然不同的觀點如何繼續提供今天的政治思想重要的教訓。
Kei Hiruta 利用大量新的檔案材料追溯了Arendt與Berlin的衝突,從他們在戰時紐約的第一次會面到 1950 年代他們不斷擴大的知識鴻溝,再到關於Arendt 1963 年在耶路撒冷的” 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書的爭議,他們最後在 1967 年的一次會議上錯過彼此接觸的機會,以及在Arendt死後Berlin對Arendt的持續敵意。 Hiruta 融合了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研究了同時連接和分裂Arendt和Berlin的關鍵問題,包括極權主義的本質、邪惡和大屠殺、人類能動性和道德責任、猶太復國主義、美國民主、英國帝國主義和匈牙利革命。但是,最重要的是,Arendt和Berlin在一個觸及人類狀況核心的問題上存在分歧:自由意味著什麼?
在現實生活中,Arendt否認Heidegger在生活和心靈之間劃了一條線。Heidegger會告訴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和死亡,現在讓我們轉向他的想法。” Ella Milch-Sheriff 的歌劇” The Banality of Love”體現了他的一些觀點,即個人是無趣的。但在這個案例和許多其他案例中,這些想法是由孕育它們的生活中的人性缺陷所塑造的——這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肯定是時候重新評估Arendt了,一位極權主義的主要哲學家,鑑於她的哲學影響力,一個聰明的變色龍,他將把自己轉變為納粹主義的知識辯護者。
“平庸Banality”當然是讓Arendt臭名昭著的名詞。她在 1960 年代初在耶路撒冷對Adolf Eichmann的審判為《紐約客》提供了緩慢的報告,標題為““The Banality of Evil邪惡的平庸”。 Eichmann是希特勒大屠殺的首席文員,他是一名將數百萬男人、女人和兒童送往死亡集中營的官員。對Arendt來說,從希特勒德國難民的角度觀察他,他只是一個遲鈍的官僚,一個無名小卒,“既不變態,也不虐待狂。 . .可怕的正常。”她覺得按照法律和邏輯,他不值得被抓捕、審判或處決。
她的立場激怒了道德哲學家,使她暴露在互聯網前的私刑暴徒面前。Arendt既沒有退縮,也沒有退縮。 她告訴她堅定的朋友Mary McCarthy,“痛苦”,只是另一種活著的方式。”在“Critical Lives series”系列的“Hannah Arendt”中,Samantha Rose Hill將Arendt重新定位為女權主義女主角,“要求苛刻、毫無歉意和固執己見”,隨時準備在她拒絕接受的學科中面對男性主導地位:在她的美國中途學術生涯,她開始將自己描述為政治作家而不是哲學家。
“當然,被表揚總是很高興,” Arendt會說,但“被理解要好得多。” Hill女士是Bard College 的Hannah Arendt政治與人文中心的助理主任,她認為Arendt的工作“現在已經成為我們遺產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期待一些東西來幫助我們進行理解工作。”不是每個人都會同意這種評估。”
即使在這麼長的時間裡——Arendt於 1975 年去世——眉毛仍然被她點燃的怒火燒焦。 Kei Hiruta 的開創性研究考察了她與溫文爾雅的英國哲學家Isaiah Berlin的關係,描繪了他們 1941 年在紐約的第一次會面,一見如故。但情況却變得糟糕了。 1958 年,倫敦出版商 Faber & Faber 詢問是否應該繼續出版Arendt的” The Human Condition《人類狀況》”一書的版本時,Berlin以經典的拆解回應:“我不建議任何出版商購買這本書的英國版權。反對的有兩點:賣不出去,不好。”
這只是熱身戰,Berlin撕碎了內容,在他的報告結束時回到了對“好”的確切含義的沉思。他繼續說道:“談到道德美德,Arendt 博士說‘基督徒要求好書’是‘荒謬的’。要求一本書應該好書是否同樣‘荒謬’?讓我們希望她這麼認為。這樣她就不會介意別人說她的書不好。”在作者拒絕信的漫長而有趣的追踪中,這封是結束所有貶低的貶低。
正如牛津大學研究員 Hiruta 先生在“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中所展示的那樣,這兩個巨人之間迄今為止尚未探索的關係之所以令人著迷,不僅是因為它正在醞釀中的爭吵,而且因為作為一對:它們和對立面一樣相似。兩人都在波羅的海沿岸成食、Arendt在Königsberg(現俄羅斯Kaliningrad)的猶太家庭中成長、而Berlin則 Latvian Riga的猶太家庭中長大。Arendt的父母對宗教漠不關心,而Berlin知道他的祖先是Lubavitch拉比。Arendt的早年生活因父親死於梅毒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中斷,這促使她搬到了柏林市。Berlin通過他在聖彼得堡的窗戶目睹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然後高興地被送到倫敦的一所私立學校。
Arendt就讀於馬爾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只會說德語,在流放期間努力學習英語。Berlin的第一語言是俄語,能說流利的拉脫維亞語、德語、意第緒語、希伯來語、法語、英語和意大利語。在擔任Covent Garden皇家歌劇院董事會成員期間,他喜歡輕浮,並撰寫有關威爾第歌劇的博學文章。Arendt沒有瑣碎的追求,沒有閒聊。Berlin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她在新學院任教,是Northwestern大學和Vassar大學的講師,但從未獲得終身教職。幾乎在每一個方面,他們都是相互支持和反對的。
Hiruta 先生巧妙地將他們在 1941 年的第一次相遇置於情境中:Arendt是一名身無分文的難民,領取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津貼,與她無業的丈夫和受撫養的母親住在兩間出租的房間裡。Berlin是丘吉爾政府的授權代表,被派往華盛頓和紐約收集信息並影響政策。但Arendt在握手之後,攻擊Berlin,因為他被認為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缺乏承諾。Chaim Weizmann的老朋友Berlin認為她是“狂熱分子”。
八年後,Arendt的著作被廣泛閱讀,她正在完成哈佛歷史學位的論文《極權主義的起源》。Arthur Schlesinger Jr. 在哈佛的一次會議上把她和Berlin一起帶到了一起。但這是一個災難性的誤判。Schlesinger總結說,她“對他來說太莊重、不祥、條頓人、黑格爾主義者”,後來他向Berlin表示祝賀,因為他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中將Arendt列為本世紀最被高估的作家之一。Berlin在第二次遭遇時震驚地發現Arendt已經對新成立的猶太國家採取了行動:“她襲擊了以色列。”
如果不是因為對Eichmann的審判,除了在學術期刊上的狙擊,這種不匹配就會結束。以色列情報機構(在西德的幫助下)追踪到布宜諾斯艾利斯,Eichmann被綁架,飛往以色列並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 1933 年,Arendt在蓋世太保的牢房裡過夜,只是勉強將她的母親從德國解救出來,她採取了行動,她認為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納粹頭目肉身的機會”。
1961 年 4 月,她參加了為期不超過一周的為期八個月的審判,駁斥了她所認為的“廉價戲劇”的大部分內容,並質疑該程序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整件事都該死的平庸,難以形容的低落和令人厭惡,”她在家裡告訴丈夫。經過兩年的醞釀,她的報告於 1963 年 2 月和 3 月出現在《紐約客》上,不久之後以書本形式出現。反應是爆炸性的。Irving Howe 和Lionel Abel在曼哈頓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組織的一次討論變成了Mary McCarthy所說的一場大屠殺,詩人Robert Lowell將其比作“一個被遺棄的家庭成員被石頭砸死”。
在Arendt的聲明中,最令人冒犯的是她聲稱,如果沒有當地猶太政要的幫助,Eichmann永遠不會謀殺這麼多人,這是一個搖搖欲墜的主張,忽略了Eichmann對這些人及其家屬的完全控制。十年後,她說:“我被 [Eichmann] 明顯的膚淺所震撼,這使得無法將他的行為無可爭議的邪惡追溯到更深層次的根源或動機。這些行為是駭人聽聞的,但行動者——至少是非常有效的一個現在正在受審——很普通,很普通,既不惡魔也不可怕。”
Arendt的傳記作者.Samantha Rose Hill 女士說: 我懷疑,在這種看法的背後,還有別的東西——Heidegger在生活和思想之間的防火牆。1946 年,Arendt飛往德國看望她的老師,這位老師在 1933 年加入納粹黨並擔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後尋求國際康復,提出要離開妻子並娶她。Arendt拒絕了,但仍然在他的控制之下,無法承認她才華橫溢的施虐者曾歌頌希特勒並將傑出的同事扔給納粹狼。她從未逃脫他的魔咒,在他 80 歲生日時發表了一篇讚美詩。Heidegger 的不道德行為使她的思想蒙上了一層陰影,並嚴重歪曲了她在Eichmann審判中的判斷。
Berlin在騷動爆發時沒有批評Arendt,並私下對她的想法表示了一些同情。但他也鼓勵《邂逅》雜誌發表Arendt與猶太神秘主義學者Gershom Scholem之間的殘酷交流,後者指責她對自己的人民缺乏愛。Arendt回答說,她永遠不會愛一個民族,只會愛她的朋友。Berlin最終同意Scholem 的觀點,即她缺乏愛心,她對Eichmann審判的描述以“近乎冷笑和惡意的語氣”為特徵。
除其他外,我們在這裡目睹的是Arendt非凡的能力,可以團結人們對她的仇恨。在他們新翻譯的信件(由 Polity Press 出版)中,Scholem和法蘭克福社會學家Theodor Adorno在共同拒絕Arendt方面達到了完美的和諧,Arendt寫了一篇關於他們的朋友Walter Benjamin的有趣文章,並希望將其視為其工作的權威。 “以Arendt為例。 . .我不妥協,”Adorno咆哮道,“不僅因為我鄙視這位女士,我認為她是個洗衣老婦,更重要的是因為我知道Benjamin對她的感受。”
在哲學的世界裡,Arendt是一個局外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壓制,而Berlin、Adorno和他們的朋友們則坐在高桌邊喝著波特酒並放下任何自以為是的女人。這些哲學家交流中散發的女性恐懼症有時令人窒息。
當一切都說完了,Arendt會因為那個可怕的詞“平庸”而被人們銘記,他一直在改變它的含義,將其與邪惡聯繫起來。就Berlin而言,他留下了一系列經久不衰的作品,從他的卡爾·馬克思的基石傳記到他的“自由散文”。他關於刺猬和狐狸的寓言作為一場智力晚宴遊戲而經久不衰。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他會咕嚕咕嚕地說。儘管Arendt很棘手,但她可能知道一件大事——個人的自由必須超越意識形態,即使個人是不可原諒的。Berlin對猶太復國主義、英格蘭和歌劇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在Eichmann的案子中,他準備好讓結果證明手段是正當的。但是,狐狸並不總是在這個故事中表現得最好。